烽火岁月中的绿色火种——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云南林业高等教育
1939年深秋,昆明呈贡,空袭警报的嘶鸣打破了滇中高原的宁静。一群身着粗布长衫的师生迅速收起黑板上的森林分布图,躲进村边的防空洞。警报解除后,他们立刻回到茅草搭建的临时教室,继续绘制云南松的生长曲线——这是西南林业大学(前身云南大学森林系)在战火中坚持办学的真实缩影。民族存亡之际,这颗绿色教育的火种,在滇云大地上顽强燃烧,开启了云南林业高等教育的艰辛历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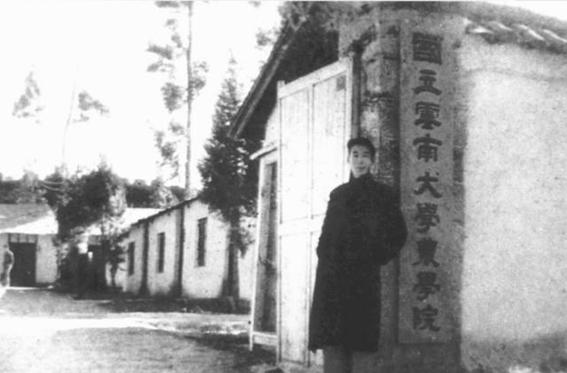
1938年国立云南大学农学院
烽火建校,国难中的林业教育萌芽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高等教育遭受重创,多所高校被迫内迁。云南作为抗战大后方,接纳了大量学术机构和学者。1938年,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审时度势,增设农学院,并于次年正式创办森林系,标志着云南高等林业教育的诞生。这一举措不仅填补了西南地区林业高等教育的空白,更肩负起“教育救国”与“实业救国”的双重使命。
首任系主任张海秋应熊庆来之邀返回云南筹建森林系。他深知,战时林业资源对支撑抗战经济至关重要——木材是铁路枕木、军工生产和民生建设的基础原料,而云南丰富的森林资源亟需科学开发与保护。
在张海秋的带领下,森林系在极端困难中迅速组建。校址选在距昆明二十公里的呈贡,既可暂避轰炸,又便于“加强学生的社会实习,促进农村建设”。师生将废弃祠堂改建为教室,用土坯垒砌实验台,借煤油灯备课阅卷。尽管物资匮乏,张海秋仍坚持高标准的办学理念,延聘多位全国知名林学家,凝聚成一个特殊的“战时学术共同体”。 许多人放弃赴欧美深造的机会,辗转千里奔赴云南,只求在边疆延续林业教育的星火。
战时办学尤其注重教学科研与抗战支援的结合。张海秋提出“学术救国与实务救国并行”,课程设置紧密呼应战时需求。除基础理论外,增设“特种用材林培育”“森林资源调查”“木材防腐技术”等实用科目。学生既学测树学、森林经理学,也掌握野外调查与林木采伐等实操技能。
为实现理论与实践结合,森林系在呈贡农场开辟实验林地,于昆明厂口建立实习林场。师生顶着空袭坚持开展造林实验、林木育种与木材性能检测。1941年,与资源委员会合建酒精原料农场,利用林业副产品生产替代燃料;为支援滇缅铁路建设,参与枕木林规划设计;应个旧锡业公司之请,规划矿场造林以防水土流失。这些实践既服务战时经济,也为学生积累宝贵经验。
1940年秋,日军加强对昆明的空袭,呈贡校区数次遭炸。一次袭击中,森林系标本室与教室被毁,珍贵标本与仪器损失惨重。师生们从废墟中抢救残存资料,用油纸仔细包裹标本,转至更隐蔽的村庄继续上课。正是这种“弦歌不辍”的坚守,使森林系在抗战期间维持正常教学,培养出一批急需的林业专才。

薛纪如(前排右二)带领学生到玉龙雪山进行森林学实习
学术突围,艰难环境中的知识创新
烽火岁月中的云南林业高等教育,不仅是知识传承的阵地,更是学术创新的摇篮。尽管设备简陋、地处边陲,学者们仍依托云南独特的生物多样性,取得多项开创性成果,为中国现代林学发展奠定基础。
植物分类学研究在战时达到新高度。秦仁昌率学生深入滇西、滇南原始森林,不畏交通阻隔与疾病威胁,采集大量标本。在简陋条件下,建立了庐山植物园丽江工作站,并在昆明逐渐形成一个新的蕨类植物研究中心。1940年,秦仁昌发表《水龙骨科的自然分类系统》一文,从蕨类植物的演变规律出发,根据系统发育理论,清晰揭示蕨类植物的演化关系,大胆提出创见,将水龙骨科划分为30多科、200多属。这一分类系统动摇了长期统治蕨类植物分类的经典体系,引起国际学界广泛关注与争论,解决了当时世界蕨类植物系统分类中的重大难题。
抗日战争期间,依托有限的条件,云大农学院开展了多项科研活动。森林学系郑万钧的树木学研究、瞿明宇智与省内外人士合作的农业合作事业推广试验、徐永椿对全省树木标本的收集及标本室建立、曾勉主持的云南椰果树资源调查、曹诚一进行的云南农作物病虫害调查等,均取得一定成绩。
上世纪40年代,徐永椿艰苦创建的森林植物标本室,为后来西南林学院标本馆成为全国乃至世界植物标本收藏较丰富的标本馆奠定了基础;薛纪如于1947年在《科学世界》发表《中国唯一之巨树——水杉》,为世人揭开水杉的神秘面纱。
尽管条件有限,森林学系仍承担了多项科研项目。到1943年,已有包括林木种子发芽试验、云南树木分类研究、桉树油提炼、除虫菊加工计划等课题。
为丰富课堂教学,抗战期间,在省主席龙云提倡学术促进教育的倡导下,开办多场与农、林、经济相关的讲座,如《云南食用菌类之研究》《云南稻作问题》《云南果品之产销问题》等。战时学术交流虽受限,森林系仍努力保持与外界的联系。张海秋凭借学术人脉,定期收到重庆、成都等地寄来的期刊资料。学者们在简陋条件下举办研讨会,交流研究成果,评阅学生论文。1943年,森林系承办中国林学会西南分会年会,川、黔、滇等地林学家齐聚呈贡,共商战时林业发展对策,成为抗战时期中国林学界的一大盛事。
学生培养秉承“少而精”的精英模式。抗战八年,森林系每年招生十至十五人,至1945年胜利,累计毕业生不足百人。学生多来自云南及周边省份,怀揣“科学救国”理想报考。在校期间需完成学业,并参与支前劳动与战地服务,养成艰苦朴素、求真务实的作风。野外实习是森林系教学的重要环节,也是锤炼意志的考验。每年寒暑假,师生组织数周野外调查,足迹遍及滇中、滇西、滇南林区。他们背负标本夹、测高仪等简易工具,徒步穿行崇山峻岭,白天采集数据,夜晚借宿山民家中整理资料、制作标本。这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教学方式,培养学生扎实的野外工作能力与深厚的行业热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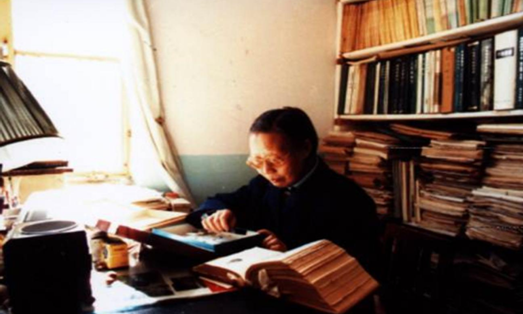
中共党员 昆虫学家 曹诚一
薪火相传,从战时学系到现代大学
抗日战争时期,森林学系就有共产党员从事革命活动。如1940年从沦陷区转来的中共地下党员曹诚一,在出色完成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同时,积极投身爱国民主运动。1941级学生杨泓光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在森林学系学习期间,一边努力学习专业知识,一边完成党交给的在云大及昆明地区开展革命活动的任务。抗战后期,杨泓光在滇黔边境组织抗日武装,并将抗日游击根据地建在沾益、盘县交界山区的播乐中学。这所学校成为当地党政干部的训练基地,杨泓光也成为云南大学最早被派到农村开展革命工作的学生之一。
抗战胜利后,云南大学森林系迎来新发展。1946年,农学院回迁昆明本部,办学条件逐步改善。张海秋等学者持续推进学科建设,增设木材学、森林保护学等课程,扩大招生规模。战火虽熄,但那段岁月凝聚的“扎根边疆、服务林业、艰苦创业、追求卓越”的精神,成为云南林业高等教育的宝贵财富。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云南林业高等教育进入新阶段。云南大学森林系在保留原有基础上,依国家建设需要进行调整与发展。1958年,云南大学农学院林学、农学两系独立为昆明农林学院,校址迁至昆明北郊黑龙潭,标志着云南林业高等教育步入独立发展的新阶段。
这所诞生于烽火岁月的林业学府,历经多次院系调整与更名,但其精神内核始终未变。1973年,昆明农林学院林学系与南迁昆明的北京林学院合并,成立云南林业学院,实现南北林学力量的强强联合。北京林学院北返后,学校保留云南林学院建制,直属国家林业部管理。1983年更名为西南林学院,成为林业部直属六所区域性林业高校之一。2010年正式更名为西南林业大学。在不同历史时期,学校始终传承“树木树人”的办学理念。

西南林业大学至真楼
绿色传承,烽火精神的当代回响
在西南林业大学校标本馆中,千千万万份动植物标本默默见证着历史——其中来自滇西抗日前线的抢救性采集标本,仿佛仍能听见隆隆枪炮声,诉说着战火中林业教育的艰难起步。“树木树人、至真至善”不仅蕴含深刻的教育理念与人文精神,抗战时期表现为“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建设时期体现为“绿化祖国、造福人民”,新时代则发展为“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实践”。
立足新时代,西南林业大学正以烽火岁月淬炼的精神为引领,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续写新篇,为培养高素质林业人才、推动科技创新、服务美丽中国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那颗从烽火中淬炼而出的绿色火种,必将在新时代燃烧得更加炽烈、更加光明。
(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作者单位:西南林业大学宣传部/编辑:程艳)